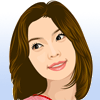 |
楼主(阅:63956751/回:0)权力还在太后手里,但国运不在【下】
190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,当时皇帝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,七天后光绪帝病逝。据恽毓鼎《崇陵传信录》记载:“帝力疾祝嘏,拜不能起立。孝钦谕左右扶掖,泣曰:‘数日不见汝,何困惫如此?’帝退倚殿西厢御床隐囊,气喘不止。”如果这段记载属实,那么病重的皇帝为太后祝寿,太后哭皇帝身体衰微,倒真是帝国斜晖中流露出的少见的母子温情。 慈禧太后以一身执掌国家权柄近50年,抚育了两位幼帝。历史学家马勇先生曾说,1888年光绪亲政,而慈禧没有立即退下来,而是继续训政若干年,这个决定为以后的政治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变数,所谓的帝党和后党就此发生。 1894年12月18日,御史安维峻上了一道奏疏,主旨是弹劾主和派大臣李鸿章,锋芒所及,竟触及西太后慈禧和她宠爱的太监李莲英。他以退为进,先表明是听说了一些市井之谈,但自己并不相信,“而又谓和议出于出于皇太后,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,此等市井之谈,臣未感深信”,因为皇太后既然已经归政皇上,还要事事牵制,“将何以上对祖宗,下对天下臣民乎”?至于李莲英,他怎么敢干预政治,“如果属实,律以祖宗法制”,哪里容得下呢? 这个折子一上,引发光绪震怒。据《翁同龢日记》记录,皇帝要把安维峻交刑部议罪,严加惩办。亏得翁同龢转圜,以为御史风闻言事,又是市井之谈,最后安维峻被革职流放。安维峻一战成名,虽因离间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获罪,却得到了当时请流派的推崇。当他被流放离开京城时,践行的人把路都堵住了,有人点赞,有人送钱,车马饮食,都有人供应。 这个事件,是甲午年和战双方对立的一次外显。清帝国正面临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之一,而垂帘听政近30年的慈禧太后,和亲政七年的光绪帝,帝国权柄名义上的最高执掌者和实际掌权者,两人之间的矛盾却由内廷外溢,由于和战之争,引发整个朝廷的对立。此后历史的走向,也受此影响,1898年戊戌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,可以说都是在此发端。 立宪派领袖张謇对晚清朝政有一段总结,他认为之所以乱象纷生,“表病在新旧,本病在后帝”,也就是说,本质矛盾在慈禧和光绪之间。“始于家庭一二离异之心,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”,于是“因异生误,因误生猜,因猜生嫌,因嫌生恶,因恶生仇,因仇生杀”,由于彼此间立场、利益不同,太后和皇帝逐渐有了误会,时间一久,就有猜疑、敌意,以致彼此嫌恶,最后竟成仇敌。在张謇看来,这也是戊戌之变和庚子之变的内在驱动力。(恶而雠,故有戊戌之变;雠而杀,故有庚子之变。戊戌雠帝雠小臣,卒雠清议;庚子杀大臣杀外人,卒杀无辜之民。” 历史的走向自然是由多因素决定,而历史学的魅力,正在于不同时期对历史事件背后的成因,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动,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在历史的迷宫中,阿里阿德涅线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晚清政潮,落点在结构性的局限上大致没错——一个前现代政权体制,又拒绝根本性的体制改革,自然无法承载近代化的疾浪狂潮。 具体在西太后和光绪帝的对立中,一般会强调她异乎寻常的权力欲望,传统的历史学家则以戊戌政变为例,声讨她绞杀了一场伟大的变革,给她打上“保守、反动”的烙印。但是,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三十余年,却又是慈禧一力支持所致。1901年她以光绪帝名义开始新政,大部分都是数年前自己亲自葬送的维新派的想法。可以说,用新与旧,维新与保守来评判这对母子并不完全适用。张謇和帝师翁同龢长相交往,而翁同龢很熟悉慈禧和光绪帝之间的情状。他的观察,应该颇合当时的实情。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,确实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严重问题。 在光绪元年,李鸿章就慨叹:“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,以待嗣皇亲政,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。焦悚莫名!”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可能不在少数,就是熬到皇帝亲政,事情就会起变化。最初可能是上一届政权和现政权之间、代与代之间的过渡矛盾,常年累月,就演变为裹挟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可调和的对立。 曾经是戊戌年局中人的王照,若干年后反思这段往事,曾有一番议论:“戊戌之变,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,其实慈禧但知权利,绝无政见,纯为家务之争。故以余个人之见,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,使得公然出头,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为伸,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。”(王照:《德宗遗事》)事实上,不过三年,太后果然主张变法了,在1901年10月2日的上谕里,太后敦促大臣们解放思想变法图强:“用是特颁懿旨,严加责成。尔中外臣工,须知国势至此,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,惟有变法自强……” 改革之中,新旧势力消长,势必引发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矛盾爆发。作为唯一具有震慑力的威权人物,是能够弥合各方势力之间的纷争,推动着新政往前走的关键人物。新旧的消长,既是时势和思想的发酵所致,又会被最高权力引导型塑。支持,或者反对,在家天下的背景中,最高领导人的价值观和见识,甚至一念之间的选择,往往决定了一场变法如何终局。 当时的一些外人,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,与不少大臣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李提摩太,1897年拜见刚毅时,就建议从外国聘请两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,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。 最终是1900年的血与火教育了庙堂中的当权者。 在逃亡途中,慈禧曾对身边人感叹:“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,现在闹到如此,总是我的错头;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人民,满腔心事,更向何处诉说呢?”(吴永:《庚子西狩丛谈》)随从的曾春煊也回忆说:“太后虽在蒙尘,困苦中尚刻意以兴复为念。一日诸人于召对之际,太后忽顾问:‘此耻如何可雪?’”(曾春煊《乐斋漫笔》) 
帖间广告位01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