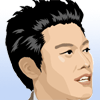 |
楼主(阅:9051017/回:0)没有掌纹的人
文:徐畅
浴室下班后,我就去了徐老爹的剃头铺,正巧建仔也在那里,他跟我吹嘘他在五月花玩了个水很大的囡儿。徐老爹在帆布条上钢了剃刀,说五月花哪有什么好货,他兄弟徐二狗在县里日弄的才算得上花魁。徐老爹一谈起兄弟徐二狗就没完没了。建仔示意我先剃,并说他随便甚时回去,老婆都不会骂。我朝他皮鞋啐了口吐沫,这狗东西分明是骂我吃软饭。我坐上转椅不理他,徐老爹给我系了围布。 你可晓得我兄弟徐二狗扛过枪?徐老爹问。 上回你讲过了。我说。 他也会剃头,李集街上没人剃得过他。徐老爹说。 说第三遍了。我说。 老爹,你是老年痴呆还是怎的?这铺子是开不了了。建仔也说。 看我这烂记性,过到下辈子去了。他说。 你弟兄那么多事,都讲尽了?建仔说。 哪能讲尽?徐老爹说,七天七宿也讲不到头。 老爹,你今天不讲个好故事,我就不剃了,闷头你看呢?建仔问我。我吐过口水算是报了仇,我不生他气。 是的,我也不剃了。我说。 怎说打就是闹的。徐老爹急了,赶紧在我耳郭边剪去一撮,那我给你们讲徐二狗剃头的事情。老爹说。建仔站起来要走,老爹不紧不慢补了一句,这回剃头,剃掉的可是人的皮。对面落地镜子里,建仔愣住了,徐老爹得意地掸去我肩头的发茬。建仔坐回条凳,徐老爹开讲了。 徐二狗剃头真是剃绝了,他剃得最好的还是光头,那一瓢秃顶就跟木匠刨过似得,滑溜溜的,一根茬也没有。 建仔不屑地哼哼鼻子。 得亏这手艺救了他一命,1938年还是1939年,日本人开到李集街,围住一街人通通枪毙了,不管大人小孩,就留了一个女的和我兄弟。你们都是新李集人,真正的李集人都叫日本人杀光了。 徐老爹换了电推子沾了机油。 我兄弟给日本人剃头,剃十个给一口干饭吃。整个剃了三天,两个排的人都剃完了,七十多个人,一个不漏。他就站在街心,日本兵排队挨个上来,也是这般转椅。但是剃完当天晚上,日本人就反剪了二狗子,塞进麻袋扎了口。扔到卡车上,不吃不喝运了两天。等他醒了爬出麻袋,四周摇摇晃晃,他自视已死,可未见无常和阎王,只有一口玻璃圆窗,窗外黑咕隆咚,他贴住玻璃才晓得,外面是没有尽头的海水。他在船舱里饿了四天,屎尿就屙拉在眼前,到了第五天,有人扔下两根老过劲的玉米,他没命地啃,煸煸就咽,门牙都掰掉了一颗。第六天,有人撒消毒液提桶洗了船舱,还搬下来座椅,座椅边镶了根铁柱,铁柱吊着三五根铁链。日本人喂二狗吃饱饭,给了他一把剃刀和一小桶浑液。小桶沉得要命。桶里是甚东西?恁沉?建仔问。 这哪能猜到。徐老爹继续说。 日本兵带了翻译跟二狗子讲清楚事儿就出去了,往后每天都有日本兵押人进来,来人坐上座椅,铁链锁住手脚,脖子绑在铁柱上。日本兵双双摁住来人,二狗子手持剃刀给他们剃头,一律光头。剃完头你们可晓得?打眉心往上两寸处,一刀划下,直抵后脑,留一指长血口,扒开头皮,提起小桶灌进去,这一步可是技术活,灌快了会溢出,灌得慢了人就死了。不快不慢才能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 活人皮?建仔倒抽一口冷风,我心里也一沉。 那东西毒着哩,水银,桶里装的是水银,水银灌进去,流经皮肉处,皮和肉就分了,待到水银流满了全身,每个脚丫、每个指头都渗满了,人皮就跟一件挂在身上的汗衫没两样,而且这会儿,人还没死。最紧要处就在这里,站一旁的士兵要不在这时抓住人的手脚,那整张人皮就全毁了,一旦抓实了,皮里的人一挣脱,头皮上的口子就大了,跐溜一下,人难耐地从皮里窜出来,在船舱里赤条条地疯跑两圈才倒头死了。 徐老爹撑开我发皱的头皮,一条条刮下去,那轻细的滋滋声听得我毛骨悚然。 就像这样,一天一个,一天一个。半个月下来,徐二狗子就疯了,等到夜里没人,他拿剃刀一刀刀划破手心,剥多少人,划多少刀,口子都是整齐的半寸长。二狗子死的时候,两只手都划花了,一道一道,跟织毛线似的,掌心的纹都没了。徐老爹收回手,取海绵擦了我的脖子,解下围布。 老爹,你胡诌呢,人皮不管吃不管喝,剥那瘆人的干甚?建仔说。 你晓得甚事?徐老爹睥睨他,做皮鞋、灯罩,还有沙发。鬼晓得还做了些甚。 建仔换了我,故事讲完了,徐老爹给建仔梳了头不说一句话,我推门而出,晚风扑进来,建仔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 你怎的了?建仔说。我回头看去,徐老爹捂住拇指,疼得脸皱成了抹布,鲜血滴滴往下落,好似没拧紧的水龙头。 喷嚏打猛了,剃刀划着手了,刀口多锋啊。建仔向我解释。我掏出一团卫生纸递给徐老爹,他揭开一层卫生纸摁住伤口。他新伤底下衬着密密麻麻的小伤疤,指头指尖虎口一处没落,鳞状的小伤疤刻得整整齐齐,满满一手。我推搡建仔,建仔惊恐地骂了句脏话,徐老爹这才反应过来,他缩回手藏进后背。建仔抢过他的另一只手,手上是同样惨不忍睹的疤痕,仿佛这双手是绞肉机里绞过,又一针针缝合的。徐老爹夺回另一只手,躲避我们的目光。 老爹,二狗子是你诌的吧?建仔问。 怎的没有,有。徐老爹哆嗦嘴唇,是个血胎,生下来就扔狗圏了,他娘的,还是我自个儿扔的,我还不到十岁。 你怎逃出来的?他们不会留你活口的,那些狗日的,对不?建仔问。 逃什么?谁留……徐老爹说。 船上,你讲的船上。建仔说。徐老爹变了脸色,脸皮恶狠狠地皱着,他一脚踢倒转椅前的镜子,玻璃摔得稀里哗啦一片。都滚,今儿个不剃了。他喷口水,连踢带踹把我们赶出铺子,他骂着,还朝我们吐口水,这回徐老爹是真的疯了。他匆忙地在门板上别了铜锁就回家了。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,也没在他的铺子里剃过头。 冬至那天,建仔来浴室泡澡,我给他搓背没收钱。我们在休息处抽烟,他说徐老爹死了。我心头一紧,问怎死的,他说是割手腕放血的,口子是整齐的半寸长,送到火葬场,身体都干了。 我默默点头,似乎他的剃刀又在我头顶一寸寸往下刮,我一口气猛吸掉半截烟。 帖间广告位01
|